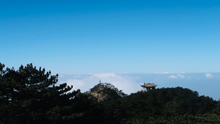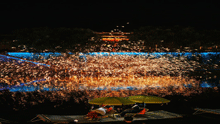平原古道
发布时间:2025-09-15来源:山东省德州市审计局作者:徐腾点击:92我总疑心,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的魂灵不在如今拓宽的柏油路上,而在那些隐于田埂间、藏在村落旁的古驿道里。这念想始于幼时听祖父讲古,他说咱平原是“九达天衢”的末梢,往南走三天到济南府,往北去两日抵德州卫,当年商贾的骡马、赶考的书生,都踩着咱这儿的土路歇脚。平原无山,一马平川的麦浪里,古道不像闽中山道那样藏于密林,它更像一条被风磨亮的丝带,顺着地势起伏,一头拴着炊烟袅袅的村落,一头连着远方的城郭。春末夏初时,麦芒擦过路面,会落下一层细碎的金粉;到了深秋,白霜又给它裹上薄纱,走在上面能听见霜粒碎裂的轻响,那是岁月在跟脚步说话。
县城往南十里有个前曹村,村口立着半截青石碑,碑上“安德古道”四个字被风雨剥蚀得只剩轮廓,却还能辨出当年的遒劲。祖父说,这碑是清朝时修的,那会儿村口的老槐树就已经粗得要两人合抱。如今老槐树还在,枝桠斜斜地覆过半个村口,树下摆着几张磨得发亮的石凳,凳面的纹路里嵌着经年累月的土屑——那是赶路人歇脚时,鞋底蹭下的故乡泥。村里的老油坊还开着,黑褐色的木门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,写着“祖传榨油”,推门进去,一股醇厚的花生香裹着木榨的沉木香扑面而来。油坊掌柜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,手上沾着永远洗不净的油星子,他说这油坊传了四代,当年古道上的马帮,路过时总要打两斤花生油,说是带着路上吃,能解乏。
我常坐在老槐树下听老人聊天,有个姓王的大爷,总爱讲他年轻时走古道的事。那会儿他才十七岁,跟着父亲往德州送棉花,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,踩着古道上的车辙印走,走累了就靠在路边的土坯房墙根歇会儿,渴了就掬一捧路边井里的水喝。“那井现在还在呢,”大爷指着村西头的方向,“井口的石头被井绳磨出了三道深沟,跟咱平原人的脊梁似的,硬挺!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去找,果然见着一口老井,井沿上的沟痕像年轮,阳光落在上面,晃得人眼晕。井旁有间塌了半边的土屋,墙面上还留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红色字迹,墙角长着几丛狗尾草,风一吹,草穗就蹭着墙面,像是在跟旧时光打招呼。
去年麦收时,我又去了前曹村,恰逢村里修水泥路,挖掘机挖到村口时,突然挖出一段青石板路——那是古道的遗迹!石板上还留着骡马蹄印,有的深,有的浅,像是一个个省略号,没说完当年的故事。村民们都围过来看,有人说这石板得好好留着,有人说要给它盖个棚子挡雨。最后,村支书决定把这段石板路留在原地,旁边种上几棵柳树,让它接着守着村子。我蹲在石板旁,摸了摸那些马蹄印,指尖能触到岁月的温度,仿佛听见当年的骡马嘶鸣,混着赶路人的吆喝,从石板缝里钻了出来。
平原的古道没有闽中山道那样的密林遮蔽,也没有古渡口连接山海,它就躺在平原上,被麦浪抱着,被炊烟绕着。它不像朱熹走过的闽中古道那样,有诗文记载,有石碑佐证,但它有自己的印记——老槐树下的石凳,老油坊的木榨,老井沿的沟痕,还有那段刚挖出来的青石板路。这些印记,都是平原人走出来的故事,是祖祖辈辈的脚步踩出来的光阴。
有一次,我带着小侄女去前曹村,她看见那段青石板路,兴奋地在上面跑来跑去,鞋底敲着石板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她问我:“伯伯,这条路能走到哪里呀?”我指着远方的麦浪说:“能走到你太爷爷年轻时去的德州,能走到你爷爷说的济南府,还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”小侄女眨着眼睛,又问:“那它有起点和终点吗?”我想了想,像祖父当年那样摸了摸她的头:“起点是咱平原的土,终点是平原人的念想,走再远,都能顺着它走回家。”
那天傍晚,我们坐在老槐树下,看着夕阳把麦浪染成金色,古道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一直延伸到天边。小侄女突然指着天上的一只麻雀说:“伯伯你看,那只鸟跟着我们呢!”我抬头一看,果然有只麻雀在我们头顶盘旋,一会儿落在槐树枝上,一会儿又飞起来,像是在给我们引路。我想起祖父说过的话,平原的每一条古道上,都住着不愿离开的魂灵,它们或许是当年的赶路人,或许是守村的老人,或许就是一只普通的麻雀,守着这片平原,守着这些走不完的路。
如今,平原县的柏油路越修越宽,汽车跑得越来越快,但我总爱绕着那些古道走。走在麦浪间的土路上,听着脚底下的土屑声响,闻着麦香混着泥土的味道,就像走在祖辈的时光里。我知道,平原的古道没有消失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——在老槐树的年轮里,在老油坊的油香里,在村民的念叨里,也在每一个平原人的心里。就像朱熹心里住着一只飞越山海的鸟,平原人的心里,也住着一条走不完的古道,它从过去走来,往未来走去,带着平原的土,带着平原的香,永远都不会停下脚步。
以上内容来自网络,如有不妥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